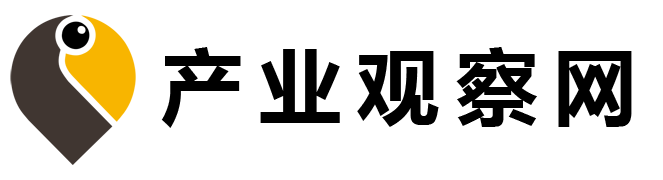2022年平安夜前一天,在家备考的沈青突然感到头痛头晕,一量体温,38.3°。当下,他脑子里蹦出两个字:完了。
第二天,发烧到38度的他前往考场。
“坐在考场上整个人忽冷忽热,三个小时考下来,我累得差点背去。”2000年出生的沈青,语气平静地回忆着自己阳着考研的经历。
与他相比,同样参加考研的两位01年学妹,周薇和杨怡幸运得多,她们考试时并没有不适,但都在考场上看到了不寻常的景象。
“考第二门政治的时候,考场上有个女生非常难受,哭着说自己要吐,想走。但我们开考是不能提早交卷的,最后来了辆救护车,一群医护人员围着守着她,一考完就把她带走了。”周薇说自己考完才出现了症状,她在和小巴描述时,仍带着浓重鼻音。
而一直没阳过的“天选之子”杨怡,则表示自己同考场的一位男生开考不到半小时,就因为实在太难受要求交卷,监考老师拒绝后,他直接弃考,之后的几门考试也没有再出现。
2022年圣诞节,474万考研人经历了一场充斥着咳嗽声、救护车警笛声的特殊考试,其中不乏沈青、周薇、杨怡这样的18、19级毕业生。
原以为封控、网课、彼此不熟悉的同学、充满遗憾的大学四年已是这群史上最难大学生的终极关卡,谁承想毕业考研遇上全面开放,“阳着考试”给青春画上了一个感叹号。
他们戏称自己为“天选大冤种”(冤种,网络流行语,常指做了傻事、倒霉的人)。而实际上,他们拥有一个更具时代标志的名字:新(冠)一代。
小巴找到不同城市、不同高校的几位“冤种”,聊了聊大学生活与疫情同行,他们到底度过了怎样的4年?在他们的故事里,遗憾、无奈是共同的情绪,而情绪之外,我们看到了“新一代”被困住的不只是行动,他们所期待的,也不只是自由。
“我染了粉色头发,
以为接下去生活都会如此缤纷绚烂”
回忆起刚入学的2018年,沈青嘴上说着快乐,但依旧鲜有情绪波动。
他印象最深的大一生活,是提前3天与父母从四川出发,在入学报到前,把南昌的著名景观点都玩了个遍。“那时候真爽,坐飞机、坐高铁都不用戴口罩。平时也会和同学聚会。”
而同样从四川出发,去杭州上学的吴欣怡显得欢脱许多,问起疫情前的大学生活,她滔滔不绝说了十分钟,甚至没给小巴留个搭话的间隙。
“我大一过得可开心了,从四川到杭州上学,第一次离家那么远,到大城市可兴奋了!特别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还和几个一起来杭州念书的高中同学聚会,出去玩。”吴欣怡的兴奋劲儿透过电话都能感受到。
“大一下学期我还参加了一个短期支教项目,天南海北的志愿者组成小队去泉州培训,然后大家又一起坐绿皮火车去湖南农村办阅读夏令营。结束后大家还在长沙玩了三天呢。”
在她的描述中,大一课程虽多,但压力小限制少,她这一年去了南京、上海、天津等各个地方旅行。
2019年年末,吴欣怡还特意染了个粉色头发,在12月31日这天和室友跑到西湖边吃着烧烤等初雪:“虽然没等到,但想着2022年开始,我的(大学)生活都会如此缤纷多彩,还是很开心。”
与18级的学长学姐相比,在19级两位学妹故事里,快乐的大学生活只有短短三四个月。
2019年9月,周薇满怀期待从老家山西来到南京。新城市、新学校的一切都令她感到兴奋:“我们学校活动非常多,迎新大会、演唱会,还有跳舞比赛和学长学姐的戏剧毕业表演。”
同一时间的山西,杨怡也正通过社团、班级团建活动努力融入新的校园生活,回忆起仅有的那几个月正常的大学生活,杨怡说像是一切刚好步入正轨就戛然而止。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在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中,发现检出SARA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这意味着新冠病毒被发现。
在这个冬天,带着一学期新鲜见闻放假回家的大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些“精彩”在未来将成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
“刚进大学,
马上就毕业了”
2022年2月,新学期开学,大学生们被通知在家上网课。
“一开始是说暂缓在家,还没有具体的返校时间,后面因为疫情严重了,返校不太安全,让我们在家上网课。”杨怡回忆道。
这一上,就是一整个学期。在小巴联系到的几位大学生记忆里,他们再次进入校园,是在期末考试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门课返校上了一节课考试了,老师也没见过,甚至连书都没有,只是在家上网课的时候听老师讲,看PPT做笔记。”杨怡表示,返校后的第一重打击便是考一场没好好上过课的试。
而对于一直身处中高风险地区的周薇来说,关于大学的大部分记忆只有上网课。
由于时常无法满足“出发地没有疫情”的返校条件,大学四年,周薇只有2个学期是在学校度过的。
线上上课的不便利之处,在她所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因其专业实操性较强,需要合作拍摄短片,而老师教学原本也需更注重线下实操的部分。
但无论在校与否,周薇和同学们一直都上着网课:“大三开始就没有笔试考试,都是合作拍片,但网课教得比较潦草,我们也没办法小组合作,对学业影响蛮大的。”
那么返校后,情况会好些吗?
根据吴欣怡的描述,2020年5月学校通知返校,在此之前,学校要求所有同学通过办公软件进入系统,进行人脸采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便是往后几年出入校园的“钥匙”。
采集完人像,在返校前48小时内做一次核酸,将核酸结果与出发地、精确到座位号的交通信息以及家长签字的返校同意书等资料一并上传学校系统,由辅导员进行人工审核。
审核通过,懵懵懂懂的大学生们便踏上了返校的旅程,吴欣怡在描述这段经历的时候用了一个词,“老实”,她说当时什么都不知道,特别老实就回学校了,一回去就封校。
之后的日子里,有的高校,学生可以通过审批,获得至少1小时至多4小时的外出时间。
而沈青所在的学校,则直到他们大四上学期,需要出校园实习,才可向辅导员申请刷脸进出。在此之前,全校学生完全封闭式管理。
被封在校园里的学生,甚至不太能够组织娱乐活动。
虽然我们时常在社交媒体刷到的“操场演唱会”“操场广场舞”,但现实中,当人员聚集越来越多,这些活动总被学校保卫处打断。与小巴沟通的毕业生无一例外提到了被学校保安驱赶的经历。
与此同时,封校让彼时的他们感到十分不解的一点是,只封学生。
“教职工、教职工家属、学校店铺的商家都可以自由进出,甚至我们学校有演播厅,会举办一些比赛,参赛人员和家属就直接巴车开进来。”吴欣怡回忆道,“说实话有埋怨过,这样封控还有什么意义?”
同样的情况,在小巴了解的其他几所高校也有发生。而定向封控的隐患,同样需要“新一代们”承担。
2022年4月,红星新闻报道宁波新增一例阳性感染者为高校教师。
5月,中国农业大学官网发布文章,称该校一名教职工核酸阳性。
7月,四川新闻网发消息称,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一名教职工在其校外居住社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
当高校教职工出现感染,学校采取的统一措施是在宿舍上网课。
“早上的课我们4个人都没起来,直接手机插上耳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关键是我们并不是被封在宿舍,还是可以在学校随意走动的,就很搞笑。”吴欣怡始终无法理解在校上网课。
这样“封校+网课”的经历,19级的毕业生或许感触更深。杨怡表示,感觉刚进大学,马上就毕业了:“大家就在大一上学期见了一下,接下来不是在家,就是在宿舍上网课,很多同学到毕业了都还不认识。”
美国心理学家沙赫特·斯坦利曾做过一个交往剥夺实验,让人待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小房间里,每待1小时,可获得15美金。参与实验的共2个人,一个待了两小时就受不了,另一个待了8天,也决定放弃。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需要社交,这一点毋庸置疑。
行动受阻的大学四年,带给“新一代”们的,不只是毕业典礼、毕业照、毕业旅行缺失的遗憾,更有缺乏社交带来的心理影响。
“给我们点时间,
找回略过的人生”
随着沟通的深入,小巴终于明白沈青这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冷静,源自哪里。
“感觉这四年,性格发生了些变化,可能封久了憋出毛病来了?”电话那头的沈青轻笑了一声,“一开始对大学生活还是充满热情和憧憬的,但现实让人觉得有些虚无,封麻了,习惯了这种日子。”
即便是在沟通中依旧热情开朗的吴欣怡,谈到封校后的心态变化,也表示即便可以申请几小时的外出,她和同学们也因时间束缚,没了出行的欲望。
除了玩儿,谈及大学,不免会联想到爱情。篮球场、白衬衫、单车后座的风、宿舍楼下的表白……校园爱情,或许是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但当小巴询问这几位年轻人关于爱情的话题,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或是单身4年,或是毕业后才找对象。
“大学第一年总看见其他学校的帅哥来宿舍楼下等女友一起去吃饭,后来不能聚集,不能出校,没地方约会,也就没有那么多情侣活动了。”吴欣怡笑着说起自己的单身观察。
而影响更深远的,是封控几乎切断了大学生与社会的所有链接。
大一刚进校,吴欣怡就加入了一个公益志愿社团。原本,社团会与其他几所学校联合,和浙残联对接,组织学习手语,做公益活动。按吴欣怡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对公益事业的热忱,也给了她拓展视野的机会。但从2020年开始,这样的活动都难以继续。
大学,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也是学生进入社会的一个重要过渡期。课余时间做兼职、与其他高效联谊、与社会组织沟通合作等等,都是大学生接触社会的“必修课”。
但18级、19级大学生,真成了象牙塔里的人。
吴欣怡告诉小巴,去年的这个时候,她海投二三十份简历,没有一点水花。今年再找工作,发现自己的位置非常尴尬:“要么,用人单位需要有工作经验的,我除了实习那几个月,没有出去工作的机会。要么,对方要19级应届生,我已经不算了。”
沈青的情况稍微好些,投的十几份简历,至少有两三条面试邀约。但当他进入面试环节,因为此前对社会接触甚少,发现自己“很傻很天真”,总被对方的思路带跑。
“还是希望用人单位不要那么‘贼’,给我们‘新一代’的毕业生一些适应社会的时间。”被各种“套路”吓怕了的沈青,最终决定考研。
另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后遗症”,是“安稳”忽然成为“新一代们”对未来的考量标准。
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高校毕业生秋招行情》数据显示,超50%的毕业生有考研打算。
在2022年度的“国考”报名结束后,国家公务员局发布公告,共有212.3万人通过资格审查,而实际录用人数是3.12万。
而到了2023年国考,共有259.77万人通过用人单位资格审查,计划招录3.71万人,报录比创历史新高。
小巴与“新一代们”对谈时,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回到2019年,你最想做什么?
沈青的答案是三个字:不折腾。他说自己曾有一个保研的机会,但想自己把控未来方向,所以拒绝了。如今找工作失利,又阳着考研,他对于当初拒绝和老师一起做项目发论文的行为,感到懊悔。
“我们才20出头,
不必感到emo”
2022年12月7日,“新十条”发布,非高风险区不再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除特殊场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
终于自由了的“新一代们”,回看自己的大学生涯,竟出人意料的理性。
“骂归骂,遗憾归遗憾,但确实有道理,我们学生出去玩跑的地方很广,老师如果注意一点,也就家和学校两点一线,比较好管控。”沈青说道。
而在学校备考的周薇也表示,考研时期开始理解学校:“你看全面开放之后崩成什么样子,我们考研人很害怕自己阳了。”据她介绍,在社会面已放开的情况下,学校仍对留校考研的大四学生进行封闭式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们安全感。
这是一群被疫情“偷走”青春的孩子,但经历过磨难,他们变得更加成熟、豁达。
对即将拥有正常大学生活的学弟学妹们,他们会说:“不管是学习还是活动,一定要积极主动去争取,好好把握社交活动,尽情享受大学生活,及时行乐。”
也会在尘埃落定后对自己说:“不必感到emo,我们才二十出头,不急,可以慢慢来。”
风雪渐止,春日将至,经历了新冠的这一代年轻人,或许需要一些阳光雨露,一些机会和耐心,来驱散封控3年带来的心理阴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