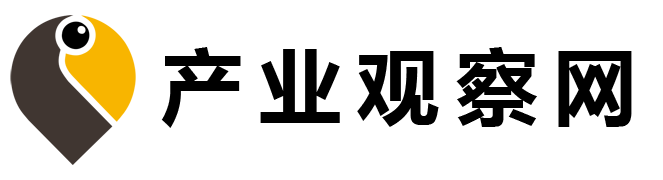在研究中国经典的过程中,我可以创造一种适合西方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与历史,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进行解读。
来源:中国新闻社
作者:杨雅惠
全文字数:2435
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名著,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多年来,《史记》研究一直吸引着众多海内外学者。东西方学者对于《史记》的研究视角有何异同?《史记》研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又有何重要意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霍尔斯特•斯科姆讲座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讲述自己如何用西方思维解读中国经典。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知名汉学家,你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汉学研究。你最初
开始了解中国,进而接触中文并对汉学产生浓厚兴趣?
倪豪士:我出生于1943年末。小时候,祖母曾给我一本她上历史课时用的旧教科书。很快,我对阅读历史书籍萌生了兴趣。在阅读《东京上空三十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这本书时,我了解到(1942年4月)美国对日本发动第一次空袭的情况。这本书描绘了美军机组在轰炸东京之后,由于缺乏足够的燃料,一些飞行员使用降落伞降抵中国的故事。这本书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人民帮助这些美国飞行员逃离日军的搜捕,并护送他们安全到重庆的经过。
这本书和其他一些像“飞虎队”(Flying Tigers)这样的故事激起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同时,这些与历史相关的书籍为我的高中历史课打下了基础。从此之后,阅读和研究传记成了我的主要兴趣。
后来我在语言学校学习了中文。我的中文名字——倪豪士,也是我在语言学校的老师为我起的。之后我选择去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深造中文。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大批华人教师,其中就有中国知名诗人和翻译家柳无忌先生。此后我去德国波恩大学(Bonn University)留学期间,又领略到一些知名汉学家的风采,由此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
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你研究《史记》至今已有30多年。就学术性和思想性而言,《史记》对西方世界有何独特魅力?你认为《史记》研究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有何重要意义?
倪豪士:我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西方在研究中文时都偏重读写,对文本的理解水平有待提高。1989年,为了提高理解能力和知识水平,我决定和同学们一起开始翻译《史记》。做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从1970年代开始《史记》研究后,发现这本书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令人满意的完整英文译本。
我认为,译介《史记》是中西方文化沟通的现实需要。《史记》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不言而喻,对于想了解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史记》本身的文学影响力也同样深远,没有完整的翻译版本将误导西方读者,因此我决定要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并尽可能具有文学性和流畅性的《史记》全译本。我希望我的《史记》译本不仅服务于一般读者,更服务于学者与专家,进一步推动西方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对于西方世界的读者来说,《史记》带他们走进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西方世界的人可以借此对古代中国形成初步的印象,进而对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中新社记者:在研究《史记》的过程中,你已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作为汉学家,你翻译和研究《史记》的方式与前人有何不同?
倪豪士:我不是独自研究或翻译《史记》,而是通过小组式的共同讨论来翻译,不仅是将中国古代汉语转换为英语,更是在用西方思维来解读中国经典。在翻译过程中,会尽力参考前人的《史记》研究成果和原有的《史记》译本,并充分利用《汉和大字典》和《康熙字典》等辞书,争取尽量准确理解每一个字的含义。
前人的译本多采用自由性翻译,尽可能少用注释,以使译文流畅,而我的译本则尽力做到准确翔实、有据可查。我希望完整再现《史记》的本真风貌,包括它的史学价值与文学风格。
民祭“史圣”大典在陕西司马迁故里韩城举行。中新社记者 田进 摄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西方研究《史记》的角度与中国学者有何不同?
倪豪士:我认为,我的汉学研究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两个本质的区别:一是,中国学者一般对中国传统著作及其作者有着更广泛深入的了解;二是,他们的母语是中文,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汉赋等中国古代文体。
对我来说,汉学研究的基础是翻译。我必须将想讨论的全部内容翻译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需要了解作品中每一个字的意思,但我至少需要搞清楚大概内容。柳无忌教授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他在撰写《中国文学概论》时,也选择将所有需要了解的作品翻译过来。而这些翻译作品都成了我们了解那些中国古典文学的途径。
同时,我在理解一些中国传统著作时,也会从西方角度加以探讨,或者将之与西方类似的文学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现象做更多层面的思考。
中新社记者:在了解和研究中国经典的过程中,你认为汉学研究对你的个人性格塑造有何影响?
倪豪士:我在研究中国经典的同时,确实深受影响。我慢慢地学会了耐心以及尊重古老的传统。同时,在中国和欧洲的一些经历也让我体会到身在异乡的感觉。因此,我试着用耐心和细心来对待那些来到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此外,我也一直试图把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传递给我的学生,不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中西方在文化认知上的差异。虽然我不可能通过研究中国经典而成为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在研究中国经典的过程中,我可以创造一种适合西方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与历史,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进行解读,这也是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
中新社记者:据你了解,诸如《史记》等中国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世界有哪些重要影响?你周围熟悉的一些人对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着怎样的认识?
倪豪士:以前,普通的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十分了解。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经典产生了兴趣。不过大多数人由于接触中文还是有困难的,所以翻译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一些在中国人看来无需解释就能明白的道理,在西方人看来可能非常难以理解。因此,对我来说,将中国经典进行准确的翻译和注释,搭建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就可以让身边更多人对中国文化典籍产生兴趣。
我的学生选择跟我一起学习和研究中国经典作品,就是因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拥有绵延5000年文明的古老国度。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倪豪士,美国汉学家,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霍尔斯特·斯科姆讲座教授,曾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德国、日本及中国多所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曾游学于远东和德国,1972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由于其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Humboldt Foundation)终身成就奖。他是美国惟一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杂志《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i.e. CLEAR)的创办者,并长期担任主编。
原标题:《倪豪士:如何用西方思维解读《史记》?| 东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