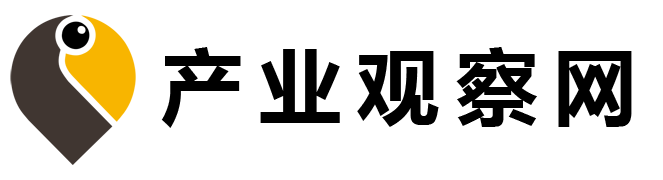能与越来越珍稀的胶片相配的,
只有香港这座城市。
来源: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全文字数:3017
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港片《七人乐队》,于7月29日在内地正式上映。这部电影从2015年就传出筹备的信息,2018年已拍完,陆续出现在很多电影节上。2020年6月,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10月,作为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2021年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七人乐队》又与《风再起时》一道成为双开幕影片,参与执导的几位导演在香港高调合体。
然而,2018年年底,导演之一的林岭东突然离世。他已制作完毕的《七人乐队》中的短片《迷路》,成为遗作。
导演 林岭东。受访者供图
这是香港动作片、新浪潮与黑帮片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们的一次集体亮相,几位加起来共获得过几十座金像奖奖杯。他们每人拍一部短片,用已退场的胶片,讲述香港过去的故事。
《迷路》单元剧照。受访者供图
作为监制和发起人,谈起这部有关香港记忆的影片,杜琪峰变得异常温柔,与那位着迷于枪火和黑帮的导演判若两人。他今年67岁,已有6年没拍过枪战片了。
杜琪峰导演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致敬菲林
2010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之后,杜琪峰不再用胶片拍电影。
胶片的退场似乎是一个时代交替的象征。杜琪峰感到惋惜,他觉得正是因为有胶片,才造就了香港电影,也造就了这一批导演和电影工作者。“我们是不是要为菲林做些事,表示对它的尊重和敬意?”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想法。
他想到去找一群导演用胶片再拍一次,这或许就是最后一次。拍什么呢?应该用最珍贵的东西拍最珍贵的故事,能与越来越珍稀的胶片相配的,只有香港这座城市。他挨个给其他导演打电话,大家都欣然同意入伙。
香港的胶片代理公司几乎已找不到了,也没有冲印的地方。他们在曼谷和台北找到了一些胶片。“浪费些时间,浪费些钱。”杜琪峰说。
最初计划是八部短片结合,每一部对应一个十年,取名《八部半》,借用费里尼经典之作的名字。但吴宇森因为身体原因中途退出,70年代成了空白。于是成了《七人乐队》,七个故事,从50年代一直拍到未来。
《回归》单元剧照。受访者供图
这70年正重叠着这一代导演的生命旅程。7个老港人,有4人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剩余3人生于50年代,最年长的是1945年出生的袁和平,今年67岁的杜琪峰年纪最小。
袁和平 (右)导演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袁和平与洪金宝成名于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动作片崛起的代表人物。70年代,李小龙、成龙相继为香港动作片奠定风格,袁与洪正是担任武指的幕后功臣。70年代末,一批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开始用镜头展现香港历史和社会经验,掀起香港电影“新浪潮”,许鞍华、徐克、谭家明是最重要的三位旗手。而杜琪峰与林岭东则是香港黑帮电影最杰出的作者,他们还都是王天林的门徒。香港电影的50年,几乎被他们概括。
洪金宝导演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作为监制的杜琪峰看完这些片子,看到了这代人之间共通的情感,也咂摸出一些不同的况味。“会觉得,哦,原来林岭东是这样想东西的,徐克是那样想的,洪金宝是这样看那个时代的,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他的语气像是沉入回忆一样缓慢下来,“加起来就会看得出——香港就是这样过来的”。
导演许鞍华。受访者供图
谭家明(前右)导演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北上南下
距离香港导演集体“北上”,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20年足以知晓“谁负谁胜出”,在杜琪峰眼里,这或许也是各人的宿命。2004年,随着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生效,陈可辛、徐克、王晶、刘伟强等香港导演陆续北上,与内地电影公司合作。杜琪峰步他们之后,2011年推出第一部合拍片《单身男女》,他将迟到的原因解释为自己的国语不好。
徐克(右二)导演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如今,徐克彻底融入内地市场,最新的作品是《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他是三名联合导演之一,刘伟强也接连执导《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而杜琪峰在2016年拍完《三人行》就调头南下,回到了港岛。
2016年6月,杜琪峰携主演钟汉良在成都为影片《三人行》宣传造势。刘忠俊 摄
电影研究者谢枫曾指出,杜琪峰的作品中始终包含着对社会的反思。在为他带来国际声誉的《黑社会》里,他真正希望谈的是时代巨变中的变与不变。第一部里,时代看似变了,但帮派信奉的还是龙头棍和叔父们,到了第二部,则是真的变化。“我要表达的是何去何从。”他说。
他自己也受到过“何去何从”这个问题的困扰。1993年,他执导了周星驰主演的《审死官》和《济公》,如日中天的周星驰在片场占据着主导,这种感觉让身为导演的杜琪峰郁闷。他放空了一整年,想明白了,电影应该是个人的东西,他决意在商业的港片世界里拍作者电影。1996年,与出自TVB的韦家辉多次深聊之后,两人成立“银河映像”,正式开工。
那时香港电影市场已经现出颓势,1993年出产了207部电影,1995年就跌到了150部,好莱坞电影呈碾压之势。在这个夹缝中,银河映像推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一个字头的诞生》《暗花》《非常突然》《枪火》《两个只能活一个》,在猛烈的暴力与死亡中间,始终弥漫着一股宁静和优雅的气息,他称之为“痛苦的浪漫”。港片衰落的十年里,银河映像撑起了面子,并且保持着港片的活力。
2016年《三人行》宣传期间,在北大的论坛上,有观众问他什么时候拍《黑社会3》,他肯定地说,一定会拍,但现在时间不对,不管到什么时候拍,“内容不会改”。他内心始终有一些笃定的东西,像一块暗礁,在潮起潮落中纹丝不动。
与《中国新闻周刊》谈到这几年时,杜琪峰表示“我当然是希望自己多些作品啦”,他说,“以我们来讲的话,应该更聪明地去拍电影。”
自由与新生
杜琪峰常常以执拗和强势示人,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他又在片场毫不留情地骂了哪位影帝。因为不满金像奖的评选机制,他毫不掩饰愤慨和失望,近20年都没再参加这个年度派对,即便组委会依然不断将提名和奖项颁给他。
但他从未真的与香港电影界分隔,反而主动怀着一股家长般的责任心,譬如这一次组织《七人乐队》这样一次集体致敬。2005年发起了“鲜浪潮短片竞赛”,亲自找投资、办培训、做监制,为香港电影挖掘新人。“鲜浪潮”计划持续了十余年,至少十位新导演浮出水面。
《遍地黄金》单元剧照。受访者供图
2016年,他亲任监制,为三位出身自鲜浪潮计划的年轻人保驾护航,拍出《树大招风》,在下一年的金像奖颁奖礼上揽获最佳影片、导演、编剧等五项大奖,他照样没有出席。
不过,他觉得年轻一代电影人欠缺了一点天马行空。这几年,《手卷烟》《浊水漂流》等几部青年导演新作收获不错的反响,再加上前些年的《踏雪寻梅》《树大招风》《一念无明》等,年轻一代香港电影人逐渐露出锋芒。与曾经百花齐放的年代对比,今时今日的港片,似乎萎缩到警匪动作片与社会写实片两种,前者负责票房,后者负责艺术。
“跟以往的电影比较,我会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在选择题目或者创作意念上很狭窄,不够开阔。”他谈到对当下创作的印象,“年轻一代比较(聚焦)社会问题,或者他们身边的实质的感觉。以往,徐克、洪金宝或者八爷(袁和平),他们很多是无中生有的。”
当然,时代已经不同了。过往武侠片、警匪片、喜剧片等各类型电影拥挤在影院时,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商业时代,彼时香港社会经济也迎来急速飞升。港片的市场不仅在本地,同时溢出到内地、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区,娱乐性是打通不同地域的金牌通行证。杜琪峰很明白今时与往昔的差异。如今港片又退回到本地市场。
往后,再有像《七人乐队》这样的集体作业,或许就要交给年轻一代了。“年轻导演的创作,我希望能够有能力支持的,能够做多些的,都希望去做。”杜琪峰说。
导演杜琪峰出席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韦亮 摄
时间总是一刻不停地往前走,告别发生在每时每刻,胶片也终究在数字时代成了古董。
“有些东西是没办法保留的,有时也会问,保留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呢?”杜琪峰仿佛自问自答,“我们只是一个平民,未必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去保留(它们)。但失去的就永远回不来,永远不会再出现,会有种可惜。”
现在,不仅找不到生产和冲印胶片的地方,连可以放映胶片的电影院也所剩无几了。所以这部用胶片拍摄的《七人乐队》,最终,还是以数字的形式放映。
原标题:《杜琪峰:再用胶片拍一次香港 | 东西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