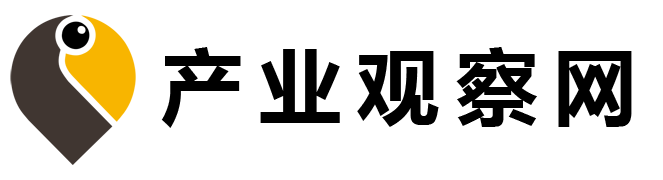三个月前,因附近一小区只允许骑手和快递员从侧门进,不准正门,他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了该小区的物业公司。 梁宁宁认为,社区侵犯了他的人格权,“涉嫌职业歧视和侮辱”。 此后,他断断续续地利用业余时间找了一位律师代表自己。
他坚持穿着亮黄色骑手工作服进入办公楼。 他来这里找律师事务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允许他随意进入大楼。 他说,附近很多写字楼和商场不允许骑手进入。 比如,有一家大型国企,不仅不让送货,而且楼下也没有外卖的桌子。 骑手只能带着东西在楼下等待; 外卖平台给他送订单的时间非常有限,超时会被扣钱。 他紧张得坐在门口的花坛上,但保安把他挡在了外面。 梁宁宁有些不服气,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心想,如果律师事务所都不让他进去,那么大多数律师事务所都不会理解他,不会受理他的案子。
该律师事务所同意代理诉讼。 7月底,该案一审开庭前夕,法院给梁宁宁打电话告知时间。 他还询问是否可以穿送餐服,想要证明“衣服不代表什么,法庭也可以进去”。 对方回复说这件衣服你可以穿,没关系。

外卖骑手梁宁宁。本文图片均来自澎湃新闻
放入系统
这是一个长宽各约500米的方形社区。 建于2004年,共有十一栋高层住宅。 “有时候一天订单很多,有时候没有。”梁宁宁说。
梁宁宁和部分同事表示,外卖平台为他们规划了路线,总是要求他们从西门作为正门进入,但实际上会被保安以“规定”为由拦下。 这将导致所有后续订单超时。 每个订单的超时罚款是三块钱,看起来并不算多。 但梁宁宁表示,一次短途旅行的总奖励可能只有四块钱。 就这样一路被关押,让他心里很不爽。
梁宁宁不是没吵过架,而是他不擅长和别人吵架。 当他与小区保安争执时,他“只能说这几句话”——“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我们不可以?” 保安说如果领导不让他们进去,他们也没办法。然后两边的火就灭了。
他从后门进去送食物。 他路过这个小区的物业,无意进去。他说自己的表达能力很差; 不过,他想了很久:“如果居住在那里的人优先进入,那么我们(家乡)村也可以阻止其他人进入?每个群体都是如此,社会就不会分裂……结束了吗?”
他依然坚持之前的送餐观点,认为所有工作都是平等的,不分门别类。 但我还是总是妥协。
今年9月28日,我和梁宁宁约在北京某大型商圈楼下见面。
这个地方已经超出了他平时的活动范围。 在午后的阳光下,现代建筑的钢化玻璃外墙看上去几乎是半透明的。 穿着工作服的梁宁宁害羞地和我一起走了进来,他的身体肉眼可见地僵硬了。
梁宁宁回忆,刚开始送外卖时,他对人很有礼貌。 有一次,一位顾客看到他的饭菜还没到,就打电话给他,说这很不尊重,“我一直向他道歉”。
现在,他对人更加严厉了。 如果有人说他送的慢,他就会说:那我就得一一送了。 然后他又会无视他们。
他还抱怨,软件中与客户在线对话的窗口只能发送实时拍摄的照片,无法发送手机相册中的图片,也无法发送截图; 事实上,他把截图给催促的顾客看,他手里还拿着这个。 如果订单很多,他们会理解的。
送餐之前,梁宁宁在江苏南通打工。 在他看来,与南通相比,北京是一个对电动汽车友好的城市。 超速和逆行交通检查没有那么严格,通常会先给予警告。 他在心里将其翻译为“对工人更加宽容”。 在他眼中,在电动车的洪流中,靠骑电动车谋生的人非常显眼,包括他广义上的同事。 黄色的衣服背后写着“美好生活小帮手”,蓝色的则是另一家公司的。 外卖平台上的骑手,黑的就是快递员,也有一些兼职的“众包”骑手,没有任何标识。
他觉得当地人骑知名品牌的电动自行车较多,送外卖、快递的则骑不知名品牌的。
梁宁宁送外卖还蛮热情的。 他感谢平台给了他“公平”——这也是很多人去大城市谋生的原因。 在工厂里,在同一条流水线上,你需要和“线长”搞好关系,才能取得高绩效。 他的社交能力有限,不擅长此。 他做这份工作已经五年了,没有多少钱支付父母的工资。
他感到内疚。 刚来北京做骑手的时候,他跑单很辛苦。 午餐送餐高峰期,订单量总是超过十个。 一上车,他就“把油门到底”,也就是把油门拧到底。 那时,“我一天几乎爬一百层楼”。 回到出租屋,不到一分钟我就睡着了。
最初几个月,他每个月能挣一万多元。 后来,他决定从站长指挥下的“专递”转向更免费的“欢乐跑”,收入也随之下降。

“公平”意味着克制,他不喜欢克制,但选择忍受。 我要求看一下梁宁宁的工作群,发现他们大多聊着有趣的事情,有时情绪失控:“这个系统一定很傻。” 没有人讨论如何在某个区域跑步,因为导航明确规定了路线:“我们如果被动接受,你有什么发言权?”
他记得2021年他第一次来北京时,下了一场大雪。 雪停后,雪很深,风吹得脸都疼了。 系统“指令满满”,不断给他分配工作,但他却做不到,只好下线。 由于他擅自下线,被扣了2000多元。 骑手联系的客服电话不一定总是能接通。 有时对方接起又挂断。 他接通了,聊了一会儿,后来退给了他一千块钱。
对于系统不理解的不合理路线和路障,“跟客服谈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问题没有办法统计”。 梁宁宁道:“他们是用他们的算法来计算的,我们一个人怎么能跟大公司说话呢?” ”
骑手使用的系统指定导航软件与地图软件有类似的界面,一条线穿过街道,连接点,并且总是按照它所说的去做。
有时当他走错路时,系统会建议梁宁宁掉头走错路,他也这么做了,尽管系统提示这是示意图,骑车人应该遵守交通规则。
退缩和妥协
梁宁宁刚到北京时,租房平台就给他找了一个小区的“半地下室”。 “半”来自于暴露在地面之上的窗户,可以让你看到外面路人的腿和脚; “冬暖夏凉”,价格也比普通隔断房便宜,梁宁宁错过了。 问题是,这个半地下室的经理要求他们必须脱掉送餐制服才能回去。 他记得管理员向他解释说,其他住户担心他将电池带进房间引发火灾。
事实上,梁宁宁的车是从路边电池柜租用电池的,不需要在室内充电,但他认为这里住的人很多,他无法逐户区分; 在这个半地下室做一些隔断出租是个好主意。 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激怒了一些不讲道理的人,他们会不断打电话投诉。 去房东那里征求意见是没有用的,他们不会在意的。 梁宁宁默默地开始脱衣服进屋,直到和她合租的骑友不小心穿到了她的衣服,两人才不得不搬家。
其实送外卖时常会遇到一些暖心的小事。 梁宁宁曾经看到顾客邻居家门口放着一箱水,上面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辛苦了,兄弟,把水拿过来喝吧”。
但也曾发生过很多次人们不喜欢他的工作服的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宁宁说她比以前更生气了。 一位朋友告诉他,他“非常愤怒,想要破坏公共财产”。 他说他也一样。
除了这种想象中的行为外,当他遇到什么事时,他会按门铃或按电梯按钮“用力按”。

骑手的工作似乎给了他广角镜头。 以前他很少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他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但自从开始送餐后,他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人:“有商家,有顾客,(街上看到的人)……”
闲暇时,梁宁宁喜欢打开一些资讯平台软件,点进去看看“骑手”新闻,然后不断向他推送类似的新闻和短视频——总有骑手被“欺负”的新闻和短视频。 ”。
梁宁宁记得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半夜,电动车不小心拖拽了别人手中的狗绳,吓到了狗。 一名陪狗主人散步的男子愤怒地斥责了他,促使他报警。 当警察过来安抚双方情绪后,他并没有坚持要求对方向他道歉。 随后他又有些埋怨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
他经常使用该平台的“点单”服务,这样他就能以比普通外卖更低的价格“团购”外卖。 他还觉得这项服务对于送餐的骑手来说不公平。 接到这样的“联单”配送任务后,骑手要给附近几个参与联单的人送餐。 配送费并不像配送一份订单的成本那么高:“但我也想(占便宜)。”
他的脑海里有什么东西在搅动。 梁宁宁渐渐想起了小时候的认真——中考后的暑假,县里的一所技工学校组织了一些初高中毕业生到外地的工厂打工,并且他也参加了。 当他读高一时,领工资时,发现被扣除了一部分。 他用打工的钱买了一部手机,在2G网上搜索县劳动局。 当他到达时,他发现它已经搬走了。 他刚刚拨打了110,询问了劳动局的新地址。
他记得劳动局的人帮他协调,学校又给了他200元,这还不是扣留的全部。
梁宁宁就读于县城一所普通高中。 学习氛围不浓,她不喜欢背文言文。 外出打工时,他从外地的书店买了几本经济、创业方面的书籍。 他很感兴趣,觉得这些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 于是他就辍学了,想去读书。
他记得年轻的时候,他和朋友们争论什么是成功。 有朋友说这要看人脉。 他觉得这应该基于智慧和远见。
他曾经和家人在南通开了一家家纺作坊,整天忙忙碌碌。 后来有客户说货物质量不好,耽误了一笔钱,耽误了他的小生意。 他无奈,只能进了工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
梁宁宁说,生意失败后,他喜欢看一些哲学书。 面对遭遇和各种他无法理解的人,他思考一个认识论问题:“为什么我这么想,他们这么想?”
更令人不解的可能是转行后他身上发生的变化。 梁宁宁曾经对规则有些执着:“以前,即使没有人,我也绝对不会闯红灯……”

电动车停车争议
只要身边还有人,就可以在系统的缝隙中制造出一些对策。
比如与梁宁宁同属一个站点的安哥告诉我,梁宁宁起诉的小区被骑手避开了。 他们确实给这个社区起了一个具有相似含义的昵称。 我一般都会收到内部的命令——“能转就转,转不了就报踢(取消),实在不行就硬着头皮发”它。”
安哥描述,当骑手到达附近时,他宁愿打电话给顾客:“对不起,你的饭菜丢了,我会补偿你的。” 他们用微信与别人私下交流,自己吃饭,而不是超时影响后面的一长串订单。
“温和”的解决方案是沿途闯红灯,逆向行驶,以走更短的路线。 “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他们的“工友”钟爷爷说。 “进小区哪扇门都是小事,公司能给我提供保险才是大事。”
骑手王海说:“(我们)也反馈给公司、12345、社区,我们都反映骑手在外地的配送时间是30分钟,所以像你们这样配送困难的社区需要去“是啊,那你得给我们50分钟吧?不然的话,就有指定地点接单了。”
代理该案的北京艾申(朝阳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飞告诉记者,今年7月,他第一次见到梁宁宁。 他穿着骑行服,表示不能进入小区。 刘飞听了梁宁宁的话。 ,首先建议他通过行政途径投诉。 梁宁宁表示,他曾向街道工会反映,但未能解决。 刘飞表达了一个想法:“即使最终确定了,执行起来也可能比较困难,而且被告也只是一个小区的人,如果遇到下一个小区你会怎么办?”
梁宁宁坚持要求法律定性。
刘飞坦言,这起民事诉讼涉及一般人格权与社区财产管理权的纠纷。 他解释说,一般人格权与肖像权、名誉权等具体人格权不同,没有明确的概念。 因此,当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时,他感到很尴尬。
不过,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却能理解梁宁宁的心情。 采访中,刘飞突然想到,就在他接到这起诉讼的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条很热的新闻:云南一些旅游团禁止律师和记者参团。 我觉得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喜欢挑剔。
刘飞表示,他是在梁宁宁提起诉讼后才开始寻求律师代理的。 此前,他心情郁闷地独自去了立案法庭。 他大概是在网上下载了一个模板,按照模板填写了12000元的精神补偿——梁宁宁告诉他,如果获得补偿,就会捐给处境困难的同事。

到今年7月刘飞和同事到现场调查时,大门已经向骑手敞开,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该案于7月24日开庭审理,被诉小区物业公司辩称,骑行人数较多,造成小区门前道路拥堵。 “交通很拥堵”,所以不能让他们在这里停车。 刘飞表示,他在现场看到过,发现骑手造成的拥堵并不严重,主要是网约车停车问题造成的。 双方就一些图片和视频进行了争论,难以达成共识。
9月28日,我在商圈外的十几名骑手中找到了梁宁宁。 他戴着口罩,遮住了半张脸。 在一大群骑手中,他完全认不出来了。 此时正是午餐送餐高峰期的尾声,商圈门口会停着很多电动车。

各个住宅区和商业区吸引了更多的电动汽车,存在停车需求。
第二天,我来到了梁宁宁起诉的小区。 西门已经对骑手开放,居民进出和网约车上下客区域停放了一些电动车,看上去有些乱。 保安表示,西门目前的规定是业主和访客可以骑自行车进入,送货人员只能步行进入。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 东北门的保安说,大家都可以从这个门进去。 据他介绍,大门不允许骑手进入。 原因是里面没有足够的空间停放电动汽车。

梁宁宁被诉的小区正门一侧。
其实这个小区还有一个南门比较难找。 这个时候可以进外卖,但不能送快递。 保安解释说,如果快递车也停在这里:“一定不会被堵住吧?这里还有孩子上学。” ”
发稿前夕,我们根据起诉书信息多次给小区物业管理打电话、发短信,但均未得到回复。
对于一些大型住宅区、商圈附近的道路拥堵问题,多位法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表示,《物权法》及各项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上述主体应设置相应区域,解决骑手、快递员的停车问题。
一位专家表示,他认为,负责妥善处理车辆的主体是管理这些骑手的物流公司。 对于小区门口电动车乱停问题,社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这是一个(社区)私权与(市)公权力交叉的问题。” 从立法角度看,过于严格地控制社区规划和管理可能不太现实。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安哥、钟爷爷、王海均为化名)